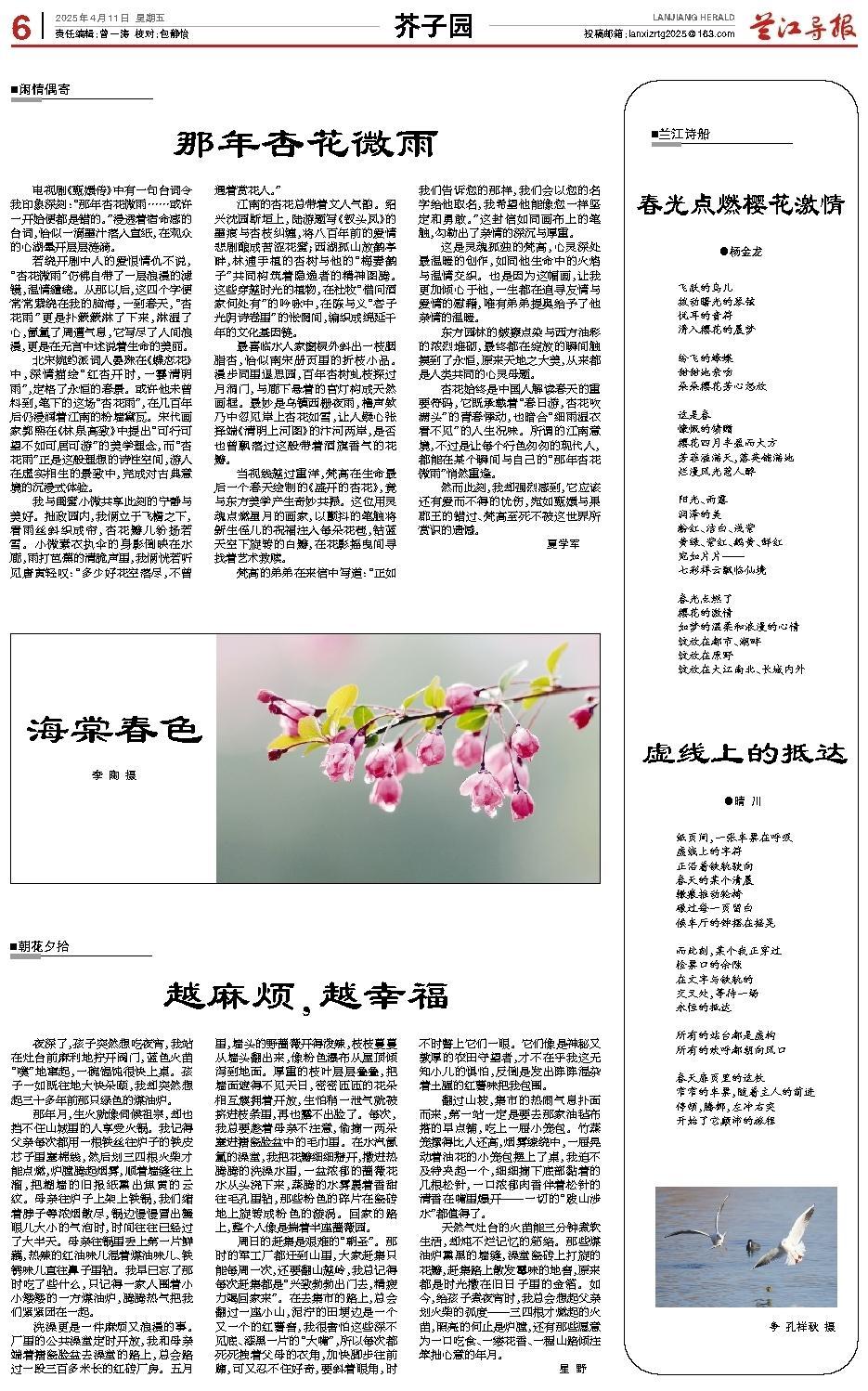越麻烦,越幸福
夜深了,孩子突然想吃夜宵,我站在灶台前麻利地拧开阀门,蓝色火苗“噗”地窜起,一碗馄饨很快上桌。孩子一如既往地大快朵颐,我却突然想起三十多年前那只绿色的煤油炉。
那年月,生火就像伺候祖宗,却也挡不住山城里的人享受火锅。我记得父亲每次都用一根铁丝往炉子的铁皮芯子里塞棉线,然后划三四根火柴才能点燃,炉膛腾起烟雾,顺着墙缝往上溜,把糊墙的旧报纸熏出焦黄的云纹。母亲往炉子上架上铁锅,我们缩着脖子等浓烟散尽,锅边慢慢冒出蟹眼儿大小的气泡时,时间往往已经过了大半天。母亲往锅里丢上第一片鲜藕,热辣的红油味儿混着煤油味儿、铁锈味儿直往鼻子里钻。我早已忘了那时吃了些什么,只记得一家人围着小小矮矮的一方煤油炉,腾腾热气把我们紧紧团在一起。
洗澡更是一件麻烦又浪漫的事。厂里的公共澡堂定时开放,我和母亲端着搪瓷脸盆去澡堂的路上,总会路过一段三百多米长的红砖厂房。五月里,墙头的野蔷薇开得泼辣,枝枝蔓蔓从墙头翻出来,像粉色瀑布从屋顶倾泻到地面。厚重的枝叶层层叠叠,把墙面遮得不见天日,密密匝匝的花朵相互簇拥着开放,生怕稍一泄气就被挤进枝条里,再也露不出脸了。每次,我总要趁着母亲不注意,偷摘一两朵塞进搪瓷脸盆中的毛巾里。在水汽氤氲的澡堂,我把花瓣细细掰开,撒进热腾腾的洗澡水里,一盆浓郁的蔷薇花水从头浇下来,蒸腾的水雾裹着香甜往毛孔里钻,那些粉色的碎片在瓷砖地上旋转成粉色的漩涡。回家的路上,整个人像是揣着半座蔷薇园。
周日的赶集是艰难的“朝圣”。那时的军工厂都迁到山里,大家赶集只能每周一次,还要翻山越岭,我总记得每次赶集都是“兴致勃勃出门去,精疲力竭回家来”。在去集市的路上,总会翻过一座小山,泥泞的田埂边是一个又一个的红薯窖,我很害怕这些深不见底、漆黑一片的“大嘴”,所以每次都死死拽着父母的衣角,加快脚步往前蹿,可又忍不住好奇,要斜着眼角,时不时瞥上它们一眼。它们像是神秘又敦厚的农田守望者,才不在乎我这无知小儿的惧怕,反倒是发出阵阵混杂着土腥的红薯味把我包围。
翻过山坡,集市的热闹气息扑面而来,第一站一定是要去那家油毡布搭的早点铺,吃上一屉小笼包。竹蒸笼摞得比人还高,烟雾缭绕中,一屉晃动着油花的小笼包摆上了桌,我迫不及待夹起一个,细细摘下底部黏着的几根松针,一口浓郁肉香伴着松针的清香在嘴里爆开——一切的“跋山涉水”都值得了。
天然气灶台的火苗能三分钟煮软生活,却炖不烂记忆的筋络。那些煤油炉熏黑的墙缝,澡堂瓷砖上打旋的花瓣,赶集路上散发霉味的地窖,原来都是时光撒在旧日子里的金箔。如今,给孩子煮夜宵时,我总会想起父亲划火柴的弧度——三四根才燃起的火苗,照亮的何止是炉膛,还有那些愿意为一口吃食、一缕花香、一程山路倾注笨拙心意的年月。
星 野